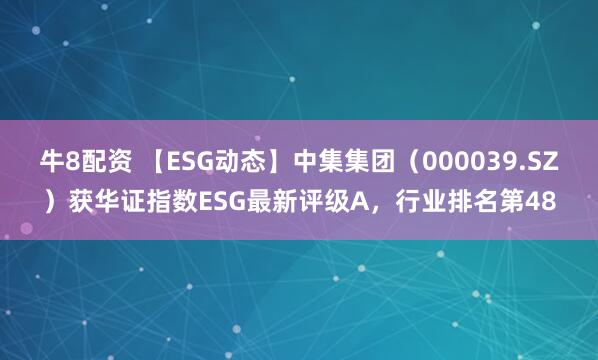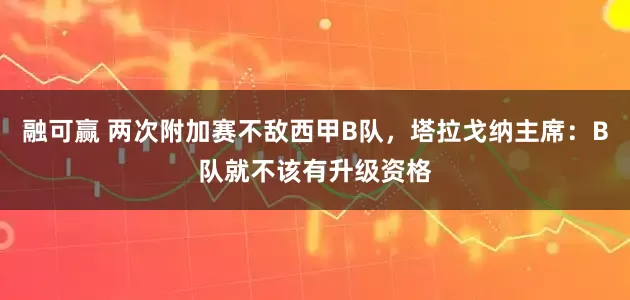文 | 高见pro翼牛网,作者 | 高贵萍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创投变迁的幅度之大让人恍如隔世。
美元基金从20世纪90年代的试水入华,到主导市场投资,再到如今的本土化发展;本土创投的萌芽、突围与裂变;双创浪潮下的狂飙与反思,硬科技主导与国资崛起。这中间穿插的看似零散的碎片故事,拼凑出一幅创投史。
从早期无序拓荒到硬科技时代系统重构,中国创投史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熵减者”的突围。
Part 01 萌芽与拓荒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漂到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海阔天空》
在历史坐标中,1993年这一节点被低估了。
这一年,熊晓鸽带着硅谷创投理念回国。彼时中国连“风险投资”一词都鲜为人知,他听到的最令他沮丧的一句话:中国风投? 听来听去就像拿着一堆大粪往墙上扔,看哪个能粘住。
这还不算,当熊晓鸽向企业家递出名片,换来的常是警惕的目光:“白送钱办企业,赚了钱就撤退,你莫不是个穿西装的骗子?”
认知鸿沟下,熊晓鸽既要寻找项目,又要承担教育市场的角色,如同开荒。开荒的两个前提:有“荒”可开,政策支持。
20世纪90年代,国家战略转型与市场机制改革共同催生了中国科技产业化浪潮。科研院所改制催生大量技术成果,但财政拨款模式难以为继,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急需市场化融资渠道,以应对“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之痛”。
为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投资,上海科投联合几家国有银行和企业,发起设立上海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3年6月与IDG合作设立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风险投资公司——上海太平洋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IDG中国前身)。
外资风投入华的序幕就此拉开。
IDG的破冰行动妙就妙在,通过“40%国资+60%外资”的股权架构设计,灵活解决了当时的外资准入难题。
换言之,以技术合资绕开外资管制,借助科技产业化需求绑定地方政府,在资本市场闭环未形成时,开创性构建“技术-资本-政策”三角平衡模型。
在早期风投像“蒙眼往混沌里扔钱”的时代,IDG根据国情放弃了硅谷式“颠覆性创新”标准,转而关注技术产业化能力,接连投资了深圳金蝶前身“爱普电脑”、科兴生物、连邦软件等企业。
1998年,成思危提交“一号提案”,直指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5%的痛点;1999年国务院7号文明确鼓励外资参与创业投资,催生的“519行情”刺激科技股热潮,又反向促进一级市场风险投资萌芽。
敏锐的外资风投,不仅接收到积极的政策信号,还嗅到互联网浪潮的味道。
国外知名公司、机构开始组建中国区团队。邝子平所代表的英特尔投资、徐新所代表的霸菱投资陆续入华。1999年孙正义向阿里巴巴注资2000万美元,霸菱投资500万美元支持网易,IDG更是连续捕获腾讯、搜狐、百度、携程等标杆项目。
2000年,《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首次定义“风险投资”法律地位。同年亚信、UT斯康达、新浪、网易、搜狐相继登陆纳斯达克,这让更多的国际风投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华登投资、富达、泛亚、兰馨亚洲、宏碁技术投资、集富亚洲等国际风投“老将”纷纷踏上中国的投资征程。
本土机构也在这一阶段陆续萌芽。1999年,深创投成立;2000年,达晨财智、同创伟业相继诞生;2001年,联想控股推出早期风险投资机构联想投资;2001年,脱胎于中金公司直投部的鼎晖投资成立。
然而,创业板的另一只靴子并没有落下。本土创投退出渠道受阻,机构们迎来第一次寒冬。仅在2002年,深圳本土创投机构和证券公司倒闭数量多达百家。
终于等到好消息。2004年5月27日,中小板开闸。这一天,新和成、江苏琼花、伟星股份、华邦制药、德豪润达、精工科技、华兰生物、大族激光等首批8家公司集体上市,释放出创投退出预期。
很快,一场特别的夏日之旅在硅谷银行的精心安排下拉开了帷幕。来自红杉资本、KPCB、Accel Partners、NEA、红点投资、DCM等顶尖风投的24位合伙人,踏上了前往北京和上海的旅途。
这趟旅程直接推动了“中国创投元年”的到来。
2005年,红杉资本与沈南鹏携手,共同创立了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张磊带着耶鲁大学捐赠的启动资金回国创办了高瓴资本。阎炎将软银亚洲的管理团队独立出来,成立了软银赛富。徐新离开霸菱投资,创办了今日资本。邓峰创立了北极光创投。朱敏则创办了赛伯乐投资……他们为创业者们搭建起通往梦想的舞台。
15年后,在北极光位于北京华茂中心的办公室,坐在我对面的邓峰语气轻快又坚定地回忆起2005年北极光成立时的初心,“我们在第一期基金募资PPT的第一页,落下白纸黑字:成就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家,培育世界级的中国企业。”
中小板开启,“股改全流通”启动,中国创投政策迎来利好。当时的邓锋感受到一个巨大的市场经济体崛起的机会正欲喷薄而出。
中国刚撞开WTO大门,一级市场中谁能架起跨太平洋的募资管道,谁就能解锁两位数的增长魔盒。
因国内IPO通道狭窄,投资逻辑以“两头在外”,即外资募资、境外退出为主。二级市场估值受国际资本影响显著。
不得不说翼牛网,这是个美元资本如潮水漫灌的掘金年代。
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同样是在2005年,湘财证券公司改制,私人金融部被裁。时任私人金融部负责人的汪静波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创业,要么各人自谋出路。
2020年时,我在诺亚控股上海总部见到了汪静波。她穿着一件中式上衣走进办公司,气场极强。当回忆起创业初始,她偏快的语气中透着一股静气,“选择创业,我们是被逼的。但如果没有诺亚,我可能就是一个懂点金融的家庭主妇。”
当时正在孕期的汪静波找到后来成为诺亚控股联合创始人、歌斐资产创始合伙人殷哲商量。殷哲回忆当时场景,“年轻是有优势的。可能也正是无惧无畏的阿Q精神,让我决定大不了从头再来,这也是一种经历。”
在“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信念感下,上海诺亚财富管理中心诞生。后来的事实证明,诺亚抓紧了市场机会。
纵观这一时期的创投市场高度分散,投资机构缺乏系统性策略,退出渠道匮乏,资本流向呈现无序竞争状态。
Part 02 双轨竞速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
---《追梦赤子心》
“现在的确是一个危急时刻…如果在花光我们给你的所有资金之前,现金流仍没什么起色的话,那就不要再回来找我们继续融资了。”2008年,红杉资本在给所投公司的信中直言。
这一年,金融危机席卷而来,资本分野。美国五大投行或倒闭,或被收购。股市暴跌,失业率飙升,消费和投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美元LP纷纷撤资。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困境往往孕育破局。而破局的关键往往掌握在未雨绸缪的一方。
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11月,政府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此时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杠杆效应逐步显现,加上社保基金等多类金融资本获准直投股权,本土机构融资渠道大为拓宽,人民币基金募资规模同比激增90%。
在某种程度上,“看得见的手”可以影响到“看不见的手”。
2006年国内首支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投基金开启了人民币基金元年;2007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引入GP/LP权责分离机制;同年A股牛市催生券商直投试点,国有资本与市场化机构形成合力。
创投也迎来鼓舞人心的信息:深创投通过同洲电子中小板上市完成本土创投首个境内IPO退出。IDG借远光软件退出打破外资机构境外垄断。人民币基金的可行性被验证。
2009年创业板开闸,首批28家企业平均涨幅106%。人民币基金的募、投、管、退全链条打通。
如上,制度创新降低了系统摩擦,缩短资本循环周期,减少资源错配导致的熵增。这些举措结合资本结构改革推动行业从边缘走向主流。
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式增长催生了新一轮财富创造浪潮。美团、饿了么、滴滴、微信、快手等陆续诞生。红杉资本则助力乡村基、麦考林等7家中国企业成功赴美上市。
2010年深创投有26家投资企业IPO上市,创下全球同行业年度IPO退出纪录。红杉中国等美元基金加速布局人民币基金,完成“双币配置”。至此,美元与人民币基金形成双轨竞逐局面。
在2010年上市的还有诺亚控股。此时走过五个年头的诺亚登陆纽交所,成为中国内地首家上市的独立财富管理机构。
汪静波、殷哲在内的几位诺亚创始人在敲钟现场相拥而泣。现场同样激动的还有沈南鹏。
在公司成立之初,诺亚为求生存,一度采取地推模式宣传和销售。2007年,红杉中国投资诺亚财富500万美元,之后推动诺亚步入发展快车道。2013年歌斐S基金诞生。如今歌斐和红杉、达晨、经纬等百家GP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2013年的创投圈迎来了一场“新生代”的崛起。英诺天使、启赋资本、银杏谷资本、清流资本、元生创投、华映资本相继成立。
还有一群勇敢的探险者从老牌机构的“大树”下走出来,开辟新天地。刘二海离开君联,创立了愉悦资本。曹毅告别红杉后创立了源码资本。张震、高翔和岳斌,这三位在IDG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携手创立了高榕资本。达晨创投出身的傅哲宽创办了启赋资本……
2014年,由江苏省国资委牵头,老牌知名投资机构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简称江苏高投集团)进行内部混合所有制改革,毅达资本诞生。同年,线性资本成立,聚焦于数据智能和前沿科技。
这一阶段,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潮涌现。京东纳斯达克上市成就了今日资本150倍回报;阿里巴巴采用VIE架构赴美上市,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一级市场PE/VC爆发;红杉中国多轮加持美团,见证其从团购平台向超级APP进化。
“全民PE”热潮下,多家本土创投从中获利。其中,九鼎在2014年至2017年进入疯狂扩张期。
2014年,九鼎集团作为首家私募机构登陆新三板,市值一度达1025亿元。高峰期管理超300亿基金,投资项目超200个,单项目回报率达10倍以上。2015年九鼎豪掷41.5亿元收购中江地产母公司,随后中江地产更名九鼎投资,成为A股首家PE上市公司。
2018年,九鼎投资复牌后市值蒸发近800亿。在金融去杠杆政策下,九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金控梦破碎。
九鼎的起落印证了私募行业从草莽到规范的必然性——当监管补位、流动性退潮翼牛网,依赖“制度缝隙”的商业模式终将崩塌。如今的九鼎鲜少参加行业活动,行事风格和之前相比变化颇大。
如果总结这一阶段的特色,你会发现,从创业板开闸到新三板扩容,制度性突破始终是行业爆发的核心动能。生态位分化,超级天使、CVC、全民PE等多元主体重塑行业格局,草莽扩张与监管补位交织演进。
当移动互联网的指数级增长遇上创业板红利,中国创投完成了从“跟随者”到“规则参与者”的身份转换,为后续硬科技黄金十年埋下伏笔。
Part 3 硬核跃迁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来自蛮荒,一生不借谁的光。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
---《孤勇者》
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全民创业热情。“互联网+”概念、电商、社交、手游、知识付费、共享经济等风口层出不穷。同年《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本土创投正式纳入国家经济战略体系。
创投圈迎来机构裂变潮。明星跨界资本与新兴基金强势入场,推动行业格局多元化。
StarVC(任泉、黄晓明等)、明嘉资本(黄晓明)、紫牛基金(张泉灵)等跨界资本涌现,利用流量与资源重构投资逻辑。资深投资人李丰成立峰瑞资本。
2016年新增近500家风投机构。创投圈“非理性繁荣”显露痕迹,典型样本莫过于2018年的“区块链”热潮。
春节是个容易迸发“奇迹”的时间节点。
“三点钟无眠区块链群”通过社群裂变迅速普及区块链概念。陈伟星与朱啸虎的“古典vs区块链”论战引发全民关注。但在2018年下半年,超99%的ICO项目破发,技术价值被投机淹没,社群迅速冷却。
泡沫破裂后,创投圈回归技术本质,区块链应用转向供应链金融、数字政务等实体场景,为后续Web3.0与数字人民币探索奠定基础。
2018年4月,资管新规出台,成为创投行业分水岭。银行理财资金撤离导致全年募资规模骤降25.7%,IPO退出数量同比减少18.46%。中小GP生存艰难。
行业也在分化。摩拜卖身、ofo破产,共享经济、无人零售、P2P等赛道频频爆雷,资本加速向半导体、新能源等硬科技领域集中。
2019年科创板的设立推动了科技企业上市潮,社保基金、地方引导基金等国资LP占比超70%。地方政府纷纷下场,其中合肥模式响彻全国——政府结合链式招商和科技赋能,实现“引进一个项目、培育一个集群、带动一方经济”的产业升级路径。
2020年,称得上是高瓴资本在一级市场布局的“高光之年”。
高瓴资本通过设立高瓴创投进行大规模募资、全产业链覆盖和精准赛道选择,成为一级市场的风向标。其布局逻辑可概括为:押注技术颠覆性(投资案例壁仞科技)、消费代际变迁(投资案例完美日记)、医疗刚性需求(投资案例百济神州)。
虽有行业人士质疑高瓴推高了赛道估值,引发泡沫争议,但高瓴的高举高打深度绑定了国产替代与消费升级趋势。
这一阶段,AI、半导体、新能源等赛道验证“超级周期”投资逻辑,一些新消费品牌也在争议中验证了长期价值。比如泡泡玛特。
早期因“潮玩伪需求”,泡泡玛特被资本市场冷落,但2020年港交所上市后其市值突破了1500亿港元。2024年营收130亿元、净利润增长188%。“情绪消费”逻辑在数据中得到验证,重塑了一级市场对Z世代消费力的认知。
受地缘政治与监管趋严影响,在2021—2023年美元基金对华投资规模从470亿美元暴跌至56亿美元。
部分美元基金在中国市场从“全球化统一品牌”向“区域独立+本土化运营”转型。
2023年6月,红杉资本宣布全球业务分拆为美欧、中国、印度/东南亚独立实体,红杉中国彻底本土化运营;9月,纪源资本(GGV)拆分为亚洲与北美机构;同月,蓝驰创投更名“Lanchi Ventures”,不再与硅谷母品牌共享“BlueRun”。
2024年,经纬创投宣布全球三大区域实体完成重命名,其中经纬中国更名为“MPC”(Matrix Partners China缩写)。官方强调并非分拆,而是通过品牌更新凸显各区域团队的独立性。
2025年3月,金沙江创投(GSR Ventures)宣布,Informed Ventures将正式接管美国业务,中国团队继续深耕本土市场。官方对此表示“不是分拆,分开品牌避免误解”。
通过分拆和更名,机构试图降低地缘风险、贴近本地市场,同时通过募集人民币基金拓展投资边界。未来,更多美元基金或效仿此类策略以维持竞争力。
这一阶段的退出渠道也有所变化。
2021年北交所开市,首批81家企业上市,打通“新三板-北交所-沪深主板”转板通道,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占比超50%。2023年全面注册制落地,硬科技企业估值体系重构,Pre-IPO套利逻辑终结。
这一阶段实现了从“模式创新”到“硬科技主导”,从“美元基金主导市场”到“国资引领”的结构性跃迁。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耐心资本”与产业链协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推手。
在中美科技博弈与国产替代需求驱动下,资本对技术熵减起到催化作用。国家政策和市场化资本形成合力,推动技术攻关与产业链整合。
Part 4 重构与跃迁
灯火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
---《灯火里的中国》
美元退潮,中东崛起,资本版图在重构。
在2024年前三季度,受美国《对华投资审查制度》及地缘政治影响,美国LP在中国风投中的参与度降至9年最低。同时,中东主权财富基金(SWFs)对华投资额逆势增长,成为美元基金重要替代资金来源。
2025年蛇年春节前后,DeepSeek火了。
DeepSeek在苹果AppStore中美下载榜中超越ChatGPT登顶。其开源策略降低了技术门槛,推动AI应用从“寡头游戏”转向“全民参与”,成为AI领域的现象级公司。
DeepSeek以557万美元训练成本实现媲美OpenAI数亿美元投入的模型性能。美股科技股震荡,英伟达单日市值蒸发5900亿美元。OpenAI等传统闭源模型厂商被迫调整策略,同时国内通义千问、百度文心等模型加速迭代,行业进入“拉力赛”阶段。
可以说,DeepSeek打破了西方技术路径依赖,在产业“无序”中开辟新秩序。早期创投聚焦“填补空白”,而当前熵减需向“创造空白”跃迁。
一级市场投资机构几乎每家都在复盘:为什么会错过DeepSeek?
集体错失暴露出传统创投机构的认知滞后:硅谷“技术-资本”叙事下,VC更关注高估值闭源模型,低估了中国企业在工程实践与场景落地的潜力。这种“小力出奇迹”路径催生新投资逻辑——技术壁垒评估从“融资规模”转向“单位算力效能”。
宇树科技是另一个值得探究的案例。
自2017年至2024年,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这位非海归、非名校背景的创业者,在早期融资时遭遇了双重困境:外界对足式机器人行业商业化前景的质疑,以及对其个人的审视。
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某顶级基金内部评估中,三位合伙人对同一项目打出了8分、7分、4分。悬殊差距不仅展现了投资人迥异的性格与价值取向,更反映了对“非典型创业者”的分歧。
事实显示,在颠覆性技术面前,偏见可能是最大的风险。
除了深度求索(DeepSeek)和宇树科技,游戏科学、云深处、强脑科技、群核科技也因技术突破和产品热度受到关注。这六家企业被称为“杭州六小龙”,频频登上国内外媒体头条。
熵减不仅是资金投入,更是资源整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以77%的融资占比领跑。区域协同经济圈从“单点突破”到“生态聚合”。
比如,杭州依托“AI六小龙”形成技术-产业联动效应;苏州凭借制造业基础在智能装备领域超越杭州;深圳通过“大院大所大企”机制,链接南方科技大学、华为等主体,孵化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的前沿项目……
退出机制亦有所创新。
2024年A股IPO数量锐减70%,倒逼退出生态重构。并购市场回暖,头部机构探索“技术分拆+战略回购+产业并购”组合路径,如北森控股拟以1.8亿元收购酷渲科技、蚂蚁集团并购好大夫在线。
S基金交易额不断创新高,北京、上海份额转让平台完善了非上市股权流动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概股回归潮下,港股凭借制度灵活性和内地资本加持成为最大受益者。
近日,恒瑞医药、宁德时代等实现“A+H”两地上市,安井食品、海天味业等超40家A股企业宣布赴港计划或已递交申请。高盛预估拼多多、富途、唯品会、满帮、好未来等总市值超万亿元的中概股,或将有资格在香港进行双重主要上市或第二上市。
国资越来越偏重“耐心赋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存续期20年)支持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长周期领域。深圳提出“万亿级‘20+8’产业基金群”。央企创投基金(如国新创投基金)以15年存续期聚焦硬科技,破解早期技术商业化难题。
“耐心资本”与市场化机构的“大胆资本”有望形成互补,推动资本从“短期套利”转向“长周期价值创造”。而长周期投资欲打破热力学第二定律,通过时间维度稀释风险,实现技术积累的熵减。
结语
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美籍华裔投资家李录将制度文明、自由市场与现代科技的融合视为现代化的核心本质。经济系统一旦与科技顺畅且高效地结合,会获得爆发式增长和持续发展的潜力。
这种潜力的释放,正是风投历经熵增,再到熵减的重要背景。在这一过程中,国资始终扮演着“秩序重构者”的角色。如今的硬科技投资浪潮,正是30年前那场破冰行动的回声。
未来中国创投行业将走向何方?
国资成为第一大出资主体且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是由现阶段国情所决定。当政策法规、创投体系日趋完善,民营创投仍有广大天地可为。
创新的生命力源于在约束中创造可能。科技术语“涌现”指系统中个体相互作用,诞生出全新性质或行为。“涌现”之道也意味着创投黄金时代必将到来。
耐心资本和时间价值则是熵减者的资本逻辑。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一级市场的“国资时代”,也恰恰为下一轮“草莽时代”埋下伏笔。
涌融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